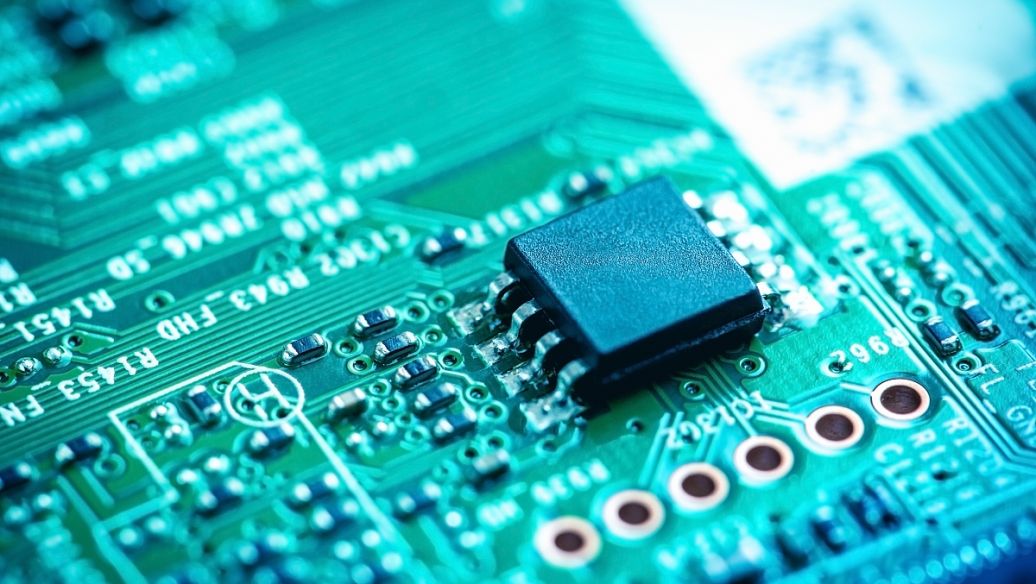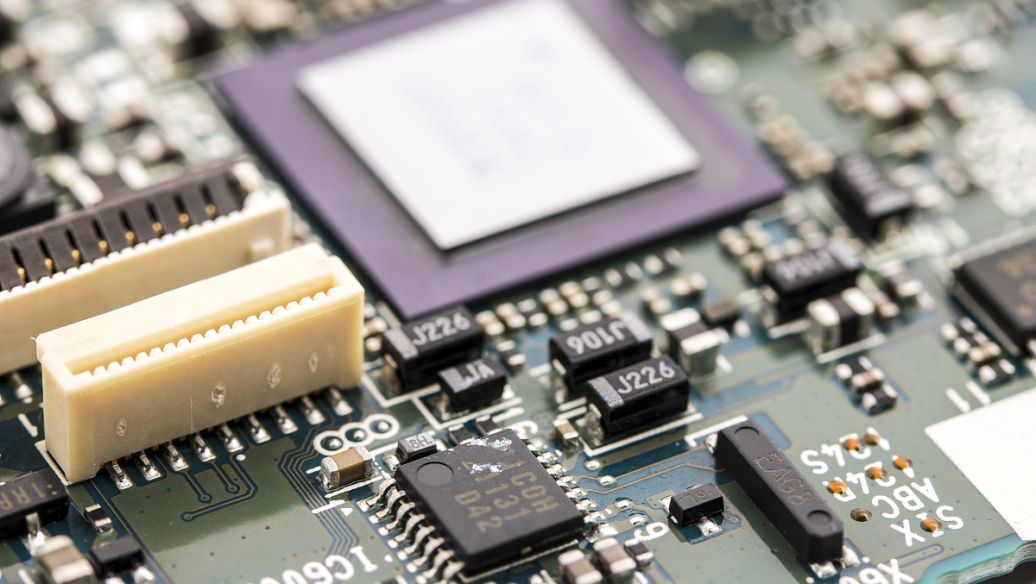按照我的理解,历史的研究,应该可以分成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记录”——原则上,史学家的工作,首先是尽可能根据事实,把历史事件用最为真实的文本系统性地编排在一起,形成一种文献。这就要求历史学家能够尽量亲历史事,或者尽量获得第一手资料。当然,历史学家在调查历史真相的过程中,不一定能够得到第一手资料,而且,即便是第一手资料,也不排除谎言或者错误记忆的情况。这就要球史学家对历史叙述进行考据,剔除虚假的部分,尽量留下真实的部分。
第二个层次是“研究”,即,根据历史记录中所反应的事件,推测事件发生的原因,评析它的意义,并且建构一种理论意义上的人类史。
显然,我们对于“夏朝”的研究,尚局限于第一个层次。因为,史学家怀疑,古代关于夏朝的整个记录都是不真实的。
也就是说,有某种证据表明,关于夏朝的记载可能整个都是不真实的。
这就不得不提到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古史”的理论。顾颉刚通过对古籍的阅读,发现了两个重要的现象:
第一个现象,“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
实际上,早在西汉时期,司马迁就曾经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他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舜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
顾颉刚说:“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
第二个现象,“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比如伏羲氏与《周易》的关系:在先秦时代,只说他“始画八卦”(《列子·杨朱》);到了隋唐时期,则说伏羲“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兴焉”(《尚书·序》);到了宋代,更有“天出文章,河出马图,于是观象于天,效法于地,近参乎身,远取诸物。兆三书、著八卦,以逆阴阳之征,以顺性命之理,成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而君民事,则阴、阳、家、国之事始明焉......”(《路史》)
对此,顾颉刚“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也就是说,在文献记录流传的过程中,很多子虚乌有的人物被安置在更早的历史脉络中;而很多被臆造的事件被赋予到很多记载不甚清晰的人物身上。
实际上,臆造历史的行为在当代也不鲜见。从世界范围来看,最典型的就是萨迦利亚·西琴的《地球编年史》以及摩利斯·科特罗的《玛雅王的圣数》;而在中国范围内,比较典型的有王大有的《三皇五帝时代》、《中华上古文明》等等。
对此,顾颉刚提出,在考据历史时,我们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在去研究某种不确定的历史记载之前,应该先研究这个记载本身的历史。或者,不严格地说,在考察一个历史记载的真实性时,看关于它的最早的记载,可靠性要强于后世对于它的记载。
这样,问题就来了:在中国最早的文献资料甲骨文中(无论是殷墟还是周原发现的),都没有关于“夏”的记载。而关于“夏”的最确切的证据,甚至晚于西周时期(唯一一个被认为出自西周、记载了夏后帝禹事迹的遂公盨是在文物市场购买,而非出土物)。由此,夏朝的存在与否就很令人生疑了。
这样,对于“夏朝”的记载的真实性,就成了我们关注的焦点。用很不全面、但也许很浅显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夏朝存在吗?
对于这个问题,有三种立场可供选择:
第一个层次是“记录”——原则上,史学家的工作,首先是尽可能根据事实,把历史事件用最为真实的文本系统性地编排在一起,形成一种文献。这就要求历史学家能够尽量亲历史事,或者尽量获得第一手资料。当然,历史学家在调查历史真相的过程中,不一定能够得到第一手资料,而且,即便是第一手资料,也不排除谎言或者错误记忆的情况。这就要球史学家对历史叙述进行考据,剔除虚假的部分,尽量留下真实的部分。
第二个层次是“研究”,即,根据历史记录中所反应的事件,推测事件发生的原因,评析它的意义,并且建构一种理论意义上的人类史。
显然,我们对于“夏朝”的研究,尚局限于第一个层次。因为,史学家怀疑,古代关于夏朝的整个记录都是不真实的。
也就是说,有某种证据表明,关于夏朝的记载可能整个都是不真实的。
这就不得不提到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古史”的理论。顾颉刚通过对古籍的阅读,发现了两个重要的现象:
第一个现象,“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
实际上,早在西汉时期,司马迁就曾经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他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舜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
顾颉刚说:“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
第二个现象,“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比如伏羲氏与《周易》的关系:在先秦时代,只说他“始画八卦”(《列子·杨朱》);到了隋唐时期,则说伏羲“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兴焉”(《尚书·序》);到了宋代,更有“天出文章,河出马图,于是观象于天,效法于地,近参乎身,远取诸物。兆三书、著八卦,以逆阴阳之征,以顺性命之理,成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而君民事,则阴、阳、家、国之事始明焉......”(《路史》)
对此,顾颉刚“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也就是说,在文献记录流传的过程中,很多子虚乌有的人物被安置在更早的历史脉络中;而很多被臆造的事件被赋予到很多记载不甚清晰的人物身上。
实际上,臆造历史的行为在当代也不鲜见。从世界范围来看,最典型的就是萨迦利亚·西琴的《地球编年史》以及摩利斯·科特罗的《玛雅王的圣数》;而在中国范围内,比较典型的有王大有的《三皇五帝时代》、《中华上古文明》等等。
对此,顾颉刚提出,在考据历史时,我们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在去研究某种不确定的历史记载之前,应该先研究这个记载本身的历史。或者,不严格地说,在考察一个历史记载的真实性时,看关于它的最早的记载,可靠性要强于后世对于它的记载。
这样,问题就来了:在中国最早的文献资料甲骨文中(无论是殷墟还是周原发现的),都没有关于“夏”的记载。而关于“夏”的最确切的证据,甚至晚于西周时期(唯一一个被认为出自西周、记载了夏后帝禹事迹的遂公盨是在文物市场购买,而非出土物)。由此,夏朝的存在与否就很令人生疑了。
这样,对于“夏朝”的记载的真实性,就成了我们关注的焦点。用很不全面、但也许很浅显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夏朝存在吗?
对于这个问题,有三种立场可供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