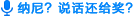最过分的是,他们光弹弹也就罢了,还对黑宇进行人身攻击,说他的麻雀(四川话管鸡鸡叫麻雀)比中华铅笔的笔芯还细,本来已经麻木了的黑宇觉得士可杀不可辱,开始嚎啕大哭。我当时正好放学路过,听见黑宇的哭声就知道他准是又被那几个发育得比较早的大孩子给弹麻雀了。我那时虽然还没发育,但是跟着我一个当兵的叔叔练过两年擒拿术,方圆几里内没有孩子敢惹我,于是我晃晃悠悠地走向上前去,一把夺过小喽啰手里的中华铅笔,转身朝着小流氓头子的屁股上就是一扎,扎得小流氓头子哇哇大哭,声如洪钟,愣是把黑宇屈辱的哭声给盖了过去。
我指着小流氓头子说:“你给我记住了,不是我扎你屁股,我是替黑宇的麻雀扎你屁股!”我高举中华铅笔作势下扎,问他记住没有?
“记住了!是黑宇的麻雀扎的!是黑宇的麻雀扎的!”小流氓头子哭喊着点头。
我拉着惊魂未定的黑宇扬长而去,在那个春天的黄昏,黑宇就像一个溺水者抓住木头一样死命握住我的胳膊,他凝视我的眼神就像成都初春的空气,潮湿而暧昧。
后来黑宇转学去了重庆,据说是因为小流氓头子回家后,家长问他屁股上的洞是怎么回事,小流氓头子言而有信地回答是被黑宇的麻雀扎的。家长跑到学校去跟老师告状,说黑宇这小子还没发育就干这种事,以后还了得。迫于学校的压力,黑宇的父亲只得带着他回了重庆万州老家。
年少纤细的黑宇没有把我给招供出来,他的麻雀替我背了十多年的黑锅,我很感激黑宇,也很想念他。
大学的时候,我在川大校园里碰到了黑宇,他穿着迷彩服,皮肤晒得黝黑,完全不复年少时白皙清秀的模样,我压根就没认出来。倒是他扑上来一把搂住我,叫我的名字。我仔细端详他的眉眼,才从那深邃而炽热的眼波里认出他竟然就是我十余年未见的发小,黑宇。
他说他在重庆读完了初高中,高考没考好,复读了一年,然后考上了川大的国防生。我有些不可思议于他的变化,他说当年承蒙我拔笔相助,对我的身手佩服得五体投地,得知我是跟着一名军人叔叔学的拳脚后,他就立志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所以报考了川大的国防生。
我指着小流氓头子说:“你给我记住了,不是我扎你屁股,我是替黑宇的麻雀扎你屁股!”我高举中华铅笔作势下扎,问他记住没有?
“记住了!是黑宇的麻雀扎的!是黑宇的麻雀扎的!”小流氓头子哭喊着点头。
我拉着惊魂未定的黑宇扬长而去,在那个春天的黄昏,黑宇就像一个溺水者抓住木头一样死命握住我的胳膊,他凝视我的眼神就像成都初春的空气,潮湿而暧昧。
后来黑宇转学去了重庆,据说是因为小流氓头子回家后,家长问他屁股上的洞是怎么回事,小流氓头子言而有信地回答是被黑宇的麻雀扎的。家长跑到学校去跟老师告状,说黑宇这小子还没发育就干这种事,以后还了得。迫于学校的压力,黑宇的父亲只得带着他回了重庆万州老家。
年少纤细的黑宇没有把我给招供出来,他的麻雀替我背了十多年的黑锅,我很感激黑宇,也很想念他。
大学的时候,我在川大校园里碰到了黑宇,他穿着迷彩服,皮肤晒得黝黑,完全不复年少时白皙清秀的模样,我压根就没认出来。倒是他扑上来一把搂住我,叫我的名字。我仔细端详他的眉眼,才从那深邃而炽热的眼波里认出他竟然就是我十余年未见的发小,黑宇。
他说他在重庆读完了初高中,高考没考好,复读了一年,然后考上了川大的国防生。我有些不可思议于他的变化,他说当年承蒙我拔笔相助,对我的身手佩服得五体投地,得知我是跟着一名军人叔叔学的拳脚后,他就立志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所以报考了川大的国防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