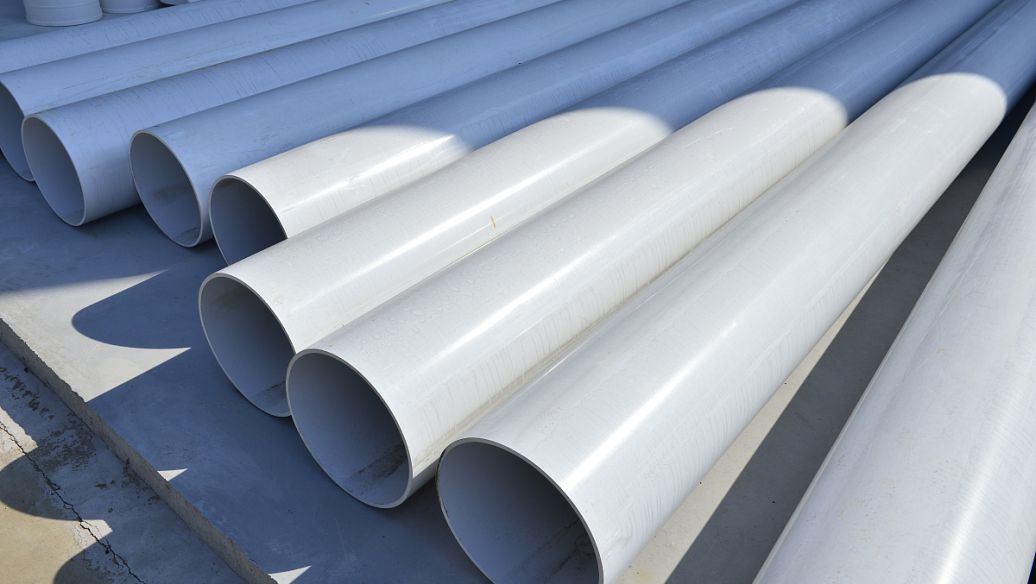萨利赫发表长文,可能是绝命书,翻译如下:
昨天,我参加了我所认识的两位最好的指挥官的葬礼,他们昨晚被杀。
现在这里的战斗很激烈,双方都有伤亡。塔利班正在使用美国弹药对付我们,黑鹰直升机正在飞来加强他们的攻击。
我没有在葬礼上发言,但其他人做了。当他们询问来自潘杰希尔山谷(阿富汗最后一个抵抗塔利班的省份)社区的数百名哀悼者是否准备继续战斗时,爆发了支持的咆哮。
人民意志坚定。他们——我们——团结一致,捍卫我们的尊严、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历史和我们对塔利班的骄傲。塔利班的士兵最近几天聚集在这里。
这个山谷的雪山位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以北约90英里处,雄伟壮观,在这里成功抵抗的历史悠久。
它在每个男人、每个女人和每个孩子骄傲的心中跳动。
现在,我们的全部重点是确保这个山谷的生存,作为对抗最近几个月控制这个国家的塔利班的基地。
生存并不一定意味着保卫领土的每一寸。而是意味着确保敌人永远不会控制这里。
我们知道我们并不孤单。其他阿富汗人与我们在一起——在附近的安达拉布山谷、卡比萨省的部分地区以及帕尔旺的口袋里。我们在全国各地都有联系,特别是在阿富汗北部和中部。
许多战士涌入这里加入民族抵抗阵线(NRF)——反塔利班战士、前阿富汗安全部队和想要阻止我们重返塔利班统治的普通阿富汗人。
因为塔利班没有赢得任何人心。他们只是利用了一位疲惫不堪的美国总统——不一定是美国本身——的有缺陷的政策,而且他们正在受到巴基斯坦臭名昭著的情报机构三军情报局的微观管理。
塔利班的发言人几乎每小时都会收到来自巴基斯坦大使馆的指示。
巴基斯坦人实际上是殖民者。但这不会持续下去,因为他们和他们的客户将无法建立正常运转的经济,或创建公务员队伍。
他们可能拥有领土控制权,但正如我们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控制土地并不一定意味着控制人民或稳定。我不认为塔利班对治理有任何想法。
西方对阿富汗的背叛是巨大的。
最近几天喀布尔机场的场景代表了人类的耻辱,自塔利班在9·11暴行之后被美国领导的联军击溃以来,任何参与阿富汗事务的国家都感到尴尬。
美国人可能吹嘘从该国撤离了大约123000人(其中6000人是美国人),但我们有4000万人。
现在,随着喀布尔机场的关闭,其他边境口岸的阿富汗人外逃仍在继续,而且情况比1980年代苏联占领期间更糟。
这不仅是拜登总统的耻辱,也是整个西方文明的耻辱。
你们的政客们知道巴基斯坦正在主持这个节目。
他们知道基地组织又回到了喀布尔街头。他们知道塔利班还没有改革。他们一直在喀布尔展示他们的自杀背心。
但西方仍有时间挽救其声誉和信誉。
拜登决心结束美国“最长的战争”,并且不再支持在我国保留甚至几千名士兵来支持我们自己的阿富汗军队——尽管我们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并听取了他自己的将军们的建议。
这是一种非常人为的挫败感,我相信,这是为了竞选的目的。但在世界各地,美国人支付的货币是他们的信誉和地位。
然而,他们有能力扭转这一局面。
20年来,西方领导人承诺不会站在阿富汗宪法上——而这正是我心中一直带着的宪法精神来到潘杰希尔山谷。
现在,我们这些聚集在这里的人正在努力维护其中的承诺。
我呼吁西方不仅给予我们道义上的支持,并在可能的情况下给予我们物质上的支持,而且还要利用这个机会推动与塔利班达成政治解决方案,该解决方案得到阿富汗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支持。
从道义上讲,西方欠每个阿富汗人。我不是求他们救我。我要求他们保住面子,保住他们的尊严,保住他们的声誉和信誉。
我为什么选择在这里?因为我相信那些在危机时刻离开自己国家的政客背叛了它的土壤。
在喀布尔崩溃之前,我得到了逃跑的机会,但我发现这种邀请令人反感。我决心打破这样一种观念,即每个阿富汗领导人只有在受保护的环境中才足够优秀。
我想追随我已故领导人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的脚步,他被称为潘杰希尔之狮,与苏联人和塔利班作战并阻止他们控制该地区。
他忍受了痛苦、挫折和危机,但他仍然以微薄的资源与他的人民在一起。
就在9·11前几天,他被伪装成记者的基地组织特工暗杀。对我来说,逃离就等于背叛了他的灵魂和他的遗产。
在喀布尔沦陷的前一天晚上,警察局长打电话给我说,监狱内发生了叛乱,塔利班囚犯正试图逃跑。
我创建了一个非塔利班的囚犯网络。我打电话给他们,他们在监狱内开始执行我的命令发动反击。
暴徒控制单位与一些阿富汗特种部队一起部署,监狱的局势得到控制。
第二天早上8点左右,我睡了几个小时后被我的警卫叫醒,他告诉我很多人试图联系我。
随着塔利班的进展变得明朗,家人、朋友、阿富汗官员、政界人士和安全当局也打来了数十个未接电话,寻求指导。
我试图联系国防部长、内政部长和他们的副手。但我找不到他们。
我确实找到了两个部委非常忠诚的官员,他们向我报告了他们如何无法将预备队或突击队部署到前线。
然后我与喀布尔警察局长交谈,他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无论他在哪里,我都希望他一切顺利。
他告诉我,东部的战线已经崩溃,南部的两个地区已经崩溃,相邻的瓦尔达克省也崩溃了。
他请求我帮助部署突击队员。我问他是否可以用他拥有的任何资源保持一个小时的防线。
他告诉我他可以。但在那绝望的一小时里,我无法在城市的任何地方找到可部署的阿富汗军队。
原因很明显。美国人在几周前曾承诺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但现在很明显这是一个毫无价值的保证。
每当我们的军队面对塔利班的集结时,美国人都会引用与塔利班谈判达成的多哈协议,说除非在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否则他们不能打击他们。
随着塔利班继续前进,这些限制毫无意义,只会强化许多人认为这场斗争是徒劳无益的观念。我无法集结任何军队来帮助警察局长。我给总统府打了电话。
我给我们的国家安全顾问发了信息,说我们必须做点什么。我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回应。到8月15日早上9点,喀布尔已经陷入恐慌。
情报局长前一天晚上来拜访我。我问过他如果塔利班袭击喀布尔他的计划。“我的计划是无论你走到哪里都和你在一起,”他说。“即使我们被塔利班阻止,我们也会一起进行最后的战斗。”
我现在找不到他了。
我相信,这些政客背叛了人民。20年来,我们一直告诉他们,我们为他们和子孙后代的未来从事一项崇高的事业。群众相信这一点,他们支持我们。他们给了我们鼓掌和尊重。
然后是同一个人恳求他们的领导人为他们挺身而出的时刻。这是一个考验的时刻。
他们现在可能会说,如果他们留在阿富汗,他们就会成为烈士。为什么不?我们需要领袖成为烈士。
他们会说他们会被俘虏。为什么不?我们需要领袖作为囚犯。
我们需要这些领导人经历阿富汗人民现在正在忍受的同样苦难。
我怎么能看到我的人民受苦,死于饥饿和口渴,赤脚行走,从安全的宫殿,然后坐在笔记本电脑屏幕后面写下它?
我是否应该期望处于边缘的穷人中最穷的人比我更有战略眼光,比我能表现出的更勇敢,期望他们拯救国家,而我只是在Facebook或 Twitter上给他们留言?
我应该接受电台采访,然后希望这些人解码我的信息并反抗吗?这是其他一些领导人所希望的。他们走了。
他们住在国外的这些酒店和别墅里。然后他们号召最贫穷的阿富汗人反抗。那是胆小鬼。如果我们想要起义,就必须领导起义。
我被情绪化的信息淹没了,邀请我逃离,做一段时间的懦夫,如果事情稳定下来,然后再跳回战斗。
那将是可耻的。我体内没有一条静脉准备接受这样的未来。
相反,我向我的导师、已故的马苏德的儿子艾哈迈德·马苏德发送了一条信息。“我的兄弟,你在哪里?” 他说:“我在喀布尔,正在计划我的下一步行动”。我告诉他我也在喀布尔并提出加入部队。
然后我翻遍了我的家,销毁了我妻子和女儿的照片。我收集了我的电脑和一些物品。我让我的首席卫士拉希姆(Rahim)把手放在我的《古兰经》上。
“拉希姆,你忠诚地为我服务,我非常感谢你,”我告诉他。'这是我最后给你的命令。把手放在《古兰经》上,保证不违背我给你的命令。
他三度承诺,全然纯洁。
“我们要去潘杰希尔,路已经修好了,”我告诉他。'我们将奋力拼搏。我们将一起战斗。
“但如果我受伤了,我有一个要求你。朝我的脑袋开两枪。我从来不想向塔利班投降。
然后我们进入了由几辆装甲车和两辆装有机枪的皮卡组成的车队。道路堵塞了。
我们艰难地越过了北关检查站,它已成为无法无天的领地——暴徒、盗贼、塔利班。我们遭到两次袭击,但我们活了下来。我们以坚定的决心奋斗了。
当我们到达潘杰希尔时,我们得到消息说社区的长老已经聚集在清真寺里。我和他们谈了一个小时,之后他们每个人都站起来支持。
20年来,潘杰希尔一直是旅游胜地。我们这里没有军事装备,没有弹药。
但那天晚上我制定了一项战略来加强该省的防御。
然后我接到一个电话,通知我艾哈迈德·马苏德正乘直升机前往潘杰希尔。我感到一股希望通过我而涌动。那天晚上我们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来制定战略。
抵抗起来容易吗?绝对不。毫无疑问,我处境艰难。我不是钢铁做的,我是人。我有情绪。我知道塔利班想要我的人头。但这是历史。我们正处于历史的中心。(正如《恶意共和国:新印度简史》的作者 Kapil Komireddi 所说的那样